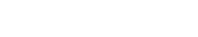第201章 宠和爱有什么区别?
第201章 宠和爱有什么区别?
天气一日比一日暖和,徐清盏也终于换上了轻薄的春装,这样一来,便愈发显得他清瘦颀长,形销骨立。
他握拳抵在唇上,咳了几声才道:“皇上息怒,臣走了这些时日,东厂和司礼监积攒了许多事情,臣这两天都在东厂,没回宫里。”
祁让听他这么说,倒是想起他早朝的时候确实不在,想必晚上歇在东厂没有回来。
“你辛苦了。”他缓和了语气,把晚余的情况简单说明,而后问道:“你觉得她这是怎么了?”
徐清盏听闻晚余生病,忍不住又咳了几声,面上浮现一些掩饰不住的担忧。
看起来好像之前确实不知道消息的样子。
“好好的怎么就病了,太医都诊不出病因的话,臣只怕也无能为力的。”他喘息着说道。
祁让观他脸色,眸光暗沉如水,片刻才道:你想不想去看看她?”
徐清盏顿了顿:“还是不去了吧,她如今回了宫,不比在外面,臣虽然是太监,规矩还是要守的。”
“你倒能忍。”祁让模棱两可地说了一句,也没有非让他去,沉吟一刻又道,“你说她会不会是装的?”
徐清盏心头一跳,脸上不动声色:“皇上此话怎讲?”
祁让说:“朕前天和她提起朝臣们希望朕去城门迎接沈长安的事,后来她就病倒了,你说她是不是装病想让朕带她去见沈长安?”
徐清盏垂在身侧的手指碾了碾,反问道:“如果真是这样,皇上会带她去吗?”
“不会!”祁让斩钉截铁,没有半分犹豫。
徐清盏摊摊手:“这不就是了,江美人那样剔透的人,怎么会猜不到皇上的心思?
她明知皇上不会带她去,何苦要装病来折磨自己,万一被皇上看穿,遭罪的还是她自己。”
“你倒是懂她。”祁让又闷闷丢出一句,心里酸酸的不是滋味。
徐清盏扯唇苦笑:“皇上其实也懂的,只是不愿意为她妥协罢了。”
祁让眸光微动,不觉皱起眉头:“朕还不够妥协吗,你知不知道你们三人干下的那些事,随便一件拎出来都可以满门抄斩了,可你们至今都还好好的活着。”
“皇上格外开恩,臣等自是感激不尽,可皇上留下臣与沈长安的性命,是单纯的怕江美人伤心难过吗?”
徐清盏虽然躬着身子,话却说得直接。
祁让脸色变了变,冷沉的凤眸看不出喜怒,也没有回答徐清盏的问话,只拧眉淡淡道:“接着说。”
徐清盏便也不怕死的接着往下说:“皇上需要沈长安那样的忠臣良将,也需要臣这把杀人的刀。
皇上所有的决定,并非出于儿女情长,因此,也称不上是为了江美人而妥协。”
这话说得确实很不客气,隐约间又有了从前那种桀骜不驯的味道。
祁让冷眼看着他,深吸一口气,又重重呼出,示意他继续往下说。
徐清盏又道:“皇上以为自己对江美人妥协到了极致,事实上,您并非对她妥协,而是对自己的心妥协。”
“什么意思?”祁让沉声问道,食指轻叩桌面,克制着没有发火。
徐清盏说:“皇上内心特别想要这样东西,无论如何都舍不得毁掉它,才一次次说服自己妥协。
就像您喜欢一只小猫小狗,它咬了您一口,或者挠了您一下,您又舍不得打死它。
只好在心里说服自己,它不懂事,它不过是个玩意儿,跟它计较什么?
可是皇上,江美人她不是个物件,也不是一只小猫小狗呀!
她是个人,是个有思想,有尊严,有自己喜好的人,不是只要一点宠爱和几根骨头就能没心没肺地活着。”
他说到激动处,停下来咳了好一阵,咳得眼中水光盈盈:“皇上,宠和爱是不一样的,您真的清楚您对她是宠还是爱吗?”
南书房里一片寂静,只有徐清盏偶尔压抑的低咳。
祁让沉着脸,默默转着手上的翡翠扳指,黑漆漆的眸底暗流涌动。
许久,他才幽幽开口道:“朕不清楚自己,倒是明白她为什么对你这么好了。”
“徐清盏,你是值得她以命相博的。”
徐清盏低着头,垂下眼睑,浓密的睫毛遮住眼中水雾。
祁让定定看他:“你说,宠和爱有什么区别?”
徐清盏敛去眼底情绪,微微抬起头:“臣自小失去双亲,孤苦无依,长大后进了宫,也未经过男女情事,懂得并不比皇上多,在臣看来,大约是爱需要尊重和空间,宠是单方面的满足和绝对的掌控吧!”
祁让又是长时间的沉默。
他恍惚想起,类似的话晚余也曾和他说过。
她说他从来没有把她当人,只当她是奴才,是禁脔,是泄欲的工具,是他高兴时搂在怀里,不高兴时就掐着脖子的小猫小狗。
她问他想要的到底是一只会摇尾巴的狗,还是一个有尊严的人。
她说他所谓的对她好,就是敲碎她的骨头,把她的尊严踩在脚下,让她永远在他面前卑躬屈膝。
她说他把她囚在宫里,不过是为了满足他畸形的占有欲,却要打着偏宠她的幌子自欺欺人。
她说他根本没有心,说他就是个没有心的暴君。
而他又是如何回答她的呢?
他说你一个外室女,也配在朕面前谈尊严?
他说他是天子,是天下主宰,就算要她做狗,也是对她的抬举。
他说她这种卑劣的女人,根本不配生他的孩子,只配被他踩在脚底,做他的玩物……
可他那都是一时的气话,并不是真的要那样对待她。
心口一阵莫名的刺痛,他张了张嘴,想解释又无从说起,许久,才艰难地问出一句:“所以,你觉得她生病是因为朕逼她太狠了吗?”
徐清盏撩衣摆跪在地上:“臣不敢妄言,臣想着,可能江美人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独处,住在皇上寝殿隔壁,终究是一种压力,皇上若真想她好,就给她一点时间和空间吧!”
祁让半眯着眼睛看他,纵然此时心里有那么一些懊悔,也没放松对他的审视。
徐清盏直挺挺地跪着,神色坦然。
祁让收回视线,捏了捏眉心,摆手道:“你去吧,容朕好好想想。”
“是。”徐清盏应了一声,躬身退了出去。
孙良言守在外面,见他出来,小声问道:“掌印大人,皇上怎么样了?”
徐清盏摇摇头:“不好说,你先不要进去,不要打扰他。”
“好,我知道了,辛苦掌印了,掌印慢走。”孙良言客气地和他道别。
徐清盏隔着宽阔的殿前广场看向正殿的方向。
他知道,此时此刻,晚余就在正殿的某间屋子里。
可他却不能去看她。
他收回视线,对孙良言微微颔首,挺直腰背,沿着廊庑向东走去。
孙良言抱着拂尘,默默望着他清瘦的背影。
春日暖风穿廊而过,吹起他轻薄的衣衫,却吹不散他周身笼罩的悲凉。
孙良言叹口气,靠回到门框上。
身处沟渠,心藏明月,这般如仙如玉的人儿,照样也跳不出这万丈红尘。
“孙良言!”祁让在里面叫了一声。
孙良言忙收起感慨,打起轻纱门帘走了进去。
“万岁爷,您有何吩咐?”